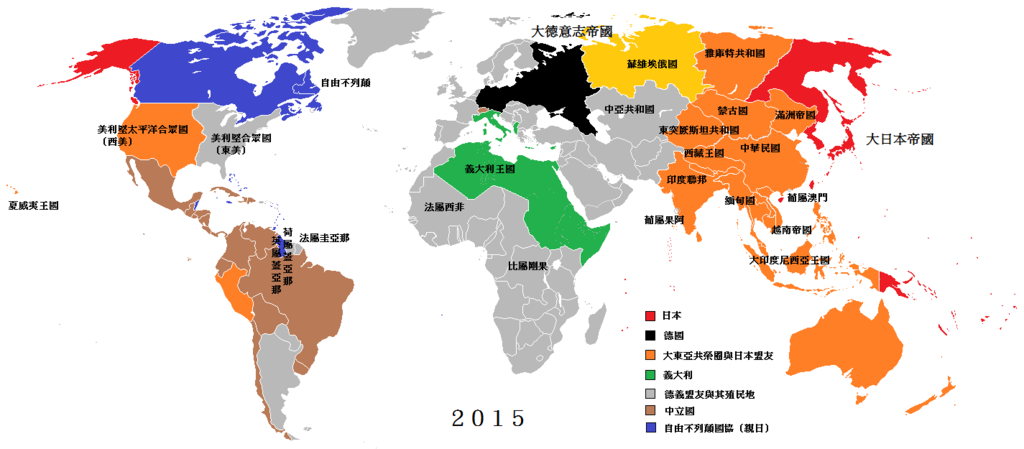我寫遊記的速度看來真的只能寫機場大全了。
-----------------------------------------------------
這次的飛行飛過白令海,穿過整個加拿大到多倫多。看著加拿大的土地我想著:天啊,北美洲就在下面。不過似乎不如之前飛法蘭克福經過西伯利亞時看著西伯利亞的土地來的感動。

其實沒有像預訂那樣到北極↑
大概飛過加拿大中部時就變成了黑夜,然後降落在夜晚的雨中的多倫多。多倫多,我到達的第一個美洲的城市。我對那裡沒什麼特別的認識,因此降落在那邊甚至不如搭遊覽車到費城時的感動那麼大,更不用說從紐澤西開進曼哈頓時那麼感動。

走經連接空橋時,我表弟德德開始跟我討論《蜘蛛人:驚奇再起2》的劇情。我當下想說回去的時候一定要看,結果也沒有看。
我走在機場,試著從各個蛛絲馬跡來分辨加拿大到底比較偏向德國還是英國(或更糟:比利時)。一開始還看不出來,到了過海關時,也看起來蠻順利的。
機場的標示都是英文法文並列。

過了海關以後,我們將我們將我們在桃園就填好的入境卡出示給一個光頭黑人,之後他會在上面做些記號,接著讓我們通過到後面的行李區。但之前在飛機上坐我們右邊的團員卻被他叫到另一個區域進行檢查,我當下覺得一定是她哪裡沒填好,不然沒道理會去其他地方啊。於是我和我爸去問那個黑人:『為什麼她去那裡?』
那個黑人給我們一個十足不耐煩的表情,說道:『因為我叫她過去。』
『她是和我們一起的,我可以跟他去嗎?』我爸指了指那個她過去的區域。
這時他似乎進入了另一種模式,一把搶過我爸的入境卡,攤開來在上面指指他已經在上面做的記號。接著似乎按壓著內心暴怒,用向幼稚園生說明『帆船四』和『大肚六』的口吻跟我爸說道:『你,去那邊。』他指向後面。接著再指向另一個檢查區域說道:『她,去那邊。』
接著我打算去找導遊,不過後來我沒找到他。他應該之後還是有出現,因為後來他似乎有解釋說那是例行抽查。
抽查。這麼簡單的概念也不打算解釋給我們聽。或許在加拿大情緒控管很差的人都在機場負責檢查。不過我也不能這麼輕易地妄下定論,可能他的狗今天早上死了吧。
不過也有可能跟我們說話的口氣或臉部表情有關。我們一臉一副『嘿,搞什麼啊』的臉去問他這個,讓他感到相當的不悅。
不管是什麼原因,我當下認為加拿大是比較偏向英國而不是德國的國家。
後來我到了行李轉盤區,地上有垃圾,角落堆放著無人認領的行李。到處都沒有看到那種在台灣或日本排的長長的行李推車。我看到阿忠舅舅推著一台。『現在好像已經沒了。』阿忠舅舅說道。
行李手推車沒了。我小心翼翼地反覆品嚐這個狀況,從來沒聽過會發生這樣的事。尤其發是在行李轉盤處根本沒幾個人的時候。
我媽叫我幫虹溪買瓶水。我拿出我在忠孝敦化台灣銀行換的加幣,兩張二十的鈔票。然而那邊的販賣機頂多只收十加幣的鈔票。於是我開始問其他人有沒有加幣的十元鈔票。阿忠舅舅沒有,問到阿公的時候就有了。
於是我把鈔票放進去買了四塊多的水。找出了加幣的硬幣,自從小學五年級繳錢時我媽誤把二元加幣當成為舊版五十元台幣而放到繳費袋以來,一直被我當作收藏品的東西。如今一次兩個從販賣機裡滾出來。在看到兩元北極熊圖案加幣滾出來的瞬間我心中頓時有種神奇但一閃而過的感覺。
大家都拿到行李後,我們出去到入境大廳。
我和子琪去旁邊的旅遊服務中心問有沒有紀念印章。我們不是唯一在那邊的人,所以必須排隊。這時有個穿灰西裝的人沒有排隊想要過去直接問他些什麼,我忘記是要問什麼,總之應該是相當好解決的事。

『你可以等我嗎?!等我回答完這位先生的問題!』旅遊服務中心僅有的員工站著大喊。用的是在台灣乃至日本的服務中心員工絕對不會使用的分貝。不過如果活在這樣不強調『客人至上』的社會,習慣了或許也是滿自在的。
等到輪到我們的時候,我們問他這裡有沒有紀念印章。『印章?』他一臉狐疑地反問。『你是指海關的那種印章嗎?』他相當認真地這樣講,讓我覺得他真心相信世界上會有人去服務中心找人蓋海關印章,而且這樣的人還有兩個。不過至少他在說的時候口氣相當良好。
但是我們沒有時間了,而且這裡看起來一副就不會擺有紀念印章的樣子。西方世界不盛行紀念印章,我想東亞盛行印章應該跟漢字的使用有關係。不過事情有壞也有好,就我在英國的經驗而言,他們比較不在乎印章是公務用或是紀念性的。在台灣或日本這些公務印章是絕對不會拿出來給觀光客收集。
總之,我們離開那裡,飛快地趕回隊伍之中。不知道是皮爾森機場的規定還是加拿大政府的規定,我們必須拖著漫長隊伍穿越馬路到達某個指定的柱子,我們的是28號柱子。為了之後再等待遊覽車過來。我們等了大約十分鐘吧,遊覽車就過來了。我們的司機是一個黑人,西追˙C˙湯斯(Cedric C. Townes)。這個名字是我看在自由女神像那天跟他聊天時看名牌得知的,不過當時其實我就忘得差不多了。我靠著模糊的記憶在一個網站上查到的,根據上面顯示,我再付0.95美元(旁邊標註著:特別優惠!Special Offer!)就可以看他的手機、訴訟紀錄和婚姻狀況。天啊。

後來遊覽車來了。
上了車之後,我們的導遊劉建國(這個名字我其實最後一天在寫導遊心得的時後才知道)提到說我們的機場和旅館都是位於密西沙加(Mississauga)市的郊區。其實在行前說明會的時候我一直以為我們的導遊是白人,因為髮型加上紅潤的皮膚吧XD。
除此之外,我注意到很嚴重的問題。那就是遊覽車上沒杯架。這怎麼可能呢?杯架不是基本配備嗎?就算沒有杯架,那至少前面應該要有類似可以摺疊的餐盤那樣的東西吧,上面會有凹下去的一塊專門用來擺飲料,結果那也沒有。
總之大約半小時後,我們下交流道。那裡看起來跟南港軟體園區那一帶很像,散散的高樓大廈,加上許多公園綠地,沒有便利商店,沒有超市。如果真的要說的話,這裡才是黑壓壓一片。

到了多倫多機場希爾頓花園飯店(Hilton Garden Inn Toronto Airport)之後,導遊去櫃檯登記入住。我和子琪在大廳晃晃,拿了一張之後根本用不到的多倫多市區地圖。

之後到房間結束了漫長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