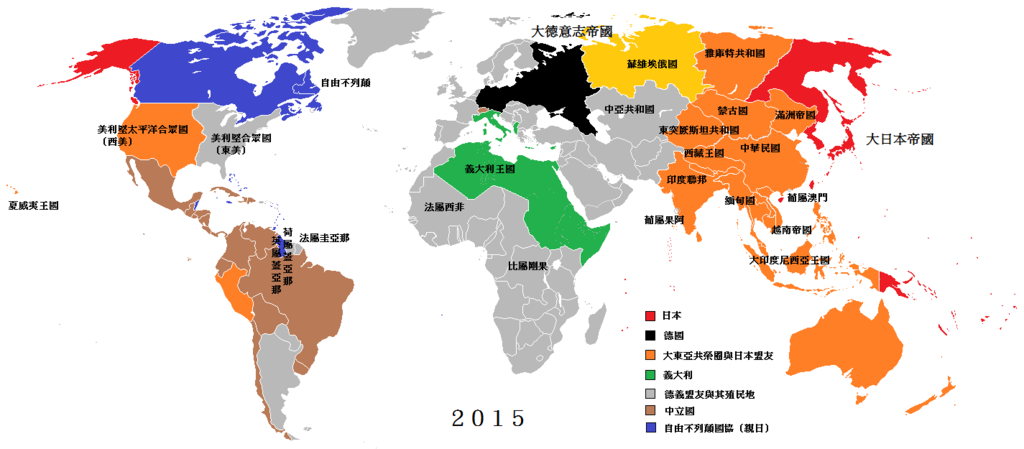從當初在五月天的歌聽到約翰˙藍儂這個名字到現在好像也有十年了,剛剛好是我目前人生的一半。現在想想還是覺得很不可思議,2004年到現在的人生怎麼可能跟出生一直到小四的時間比啊?2004年只不過是稍微久一點以前的事啊。
總之呢,我對約翰˙藍儂的認識是那種刮刮樂式的認識。從五月天的〈約翰藍儂〉,到向達倫《惡魔賊》裡的雷茲提到披頭四,再到《黑塔》三不五時就提到的《Hey Jude》(雖然是保羅唱的XD)。後來我終於在九年級考完第一次基測後挖出了家中披頭四的精選輯《1》來聽,整個高中到大學我買了不少張披頭四的專輯。九年級下學期當我在準備我根本不該準備的第二次基測時,我聽《Sg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高中暑假我在輕井澤買了他們的精選輯《1967-1970 Disc 1》。升高二的暑假在誠品旗艦買的《White Album》(或是說披頭四同名專輯XD)高二下子琪在情人節送我《Rubber Soul》,以及在升大學暑假的七夕送我《Help!》。升大二的暑假七月到了真正的倫敦的Abbey Road(但現在覺得東京某些地方還更像專輯封面一點)。而又好像是覺得去了Abbey Road卻沒聽過那整張專輯有點怪怪的,當年九月就在東京吉祥寺的Book Off買了《Abbey Road》。披頭四的音樂和約翰藍儂可以說一起貫穿了我十五歲到二十歲的生活,
而在今年八月在紐約中央公園到了草莓園,這個名字借自他們的〈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就位於他1980年12月8日被槍殺掉的地點不遠處。但當下我卻沒辦法靜下來好好地感受,因為那裡是紐約,就像夢裡的場景,我心裡總有某處不相信我真的在紐約。如果我在紐約的那幾天真的意識到我在紐約,我大概會一直跳來跳去對著子琪不斷大喊:『我們在紐約欸紐約!』
但我對約翰˙藍儂的認識就是那些歌,和一些大概的理念而已。我並沒有徹底地研究他的一生,甚至他自己唱的歌也沒聽幾首。我想我只是喜歡他在披頭四裡的歌,和他的理念。我想就是因為約翰˙藍儂,大概還有史蒂芬金跟諷刺意味濃厚的海綿寶寶,我在國中的時候心中就種下了思想左傾的種子,或多或少決定了我現在的這副德性。『都要怪你,在我心中播了種,一把吉他,就想對抗萬千炮火。』或許阿信也是這樣吧XD。
每年的這個時候都在想這個其實我不甚了解的人。比起前幾年的這些時候,我並沒有離夢想比較近,甚至連在軌道上都不算。過去想著約翰˙藍儂的時候,我總是可以很有自信地告訴自己也是朝著夢想前進,但現在好像不是這樣。我以前可以奮力衝向終點,但現在我必須像個小丑一邊耍雜耍一邊慢慢地過去,再一邊看著自己手上的球一個個失手掉落。我必須盡快找個好藉口,好讓我繼續耍雜耍下去。不然我會不斷地去想我幹嘛耍雜耍,接著把這些球都仍到外太空,一邊手插著口袋吹著〈Nowhere Man〉掉頭就走。
Doesn't have a point of view. Knows not where he's going to. Isn't he a bit like you and me?
RIP, John Lennon.